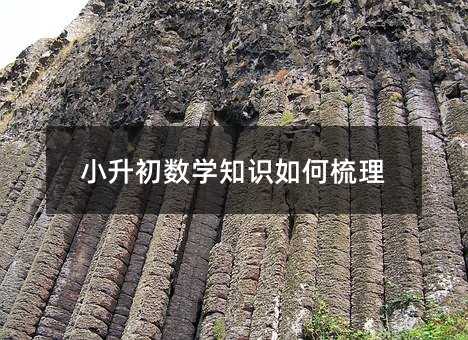岁末年初科学界的整理不断展开,去年年初揭秘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。
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,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《晶体学报》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,被一次性撤销。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。
事实上,即使在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,算数目、比速度,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。一些还算好但并不是真的突出的发现,由于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,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很大的支持。
近年来,国内科研论文发表数目突飞猛进。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,国内科技职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目,已经超越美国,位居世界第一。然而据统计,这类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。真的非常好的论文,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。
日前,中国年轻人报记者就科学界怎么样潜心学术、摒弃急于求成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。他一直坚持科研的水平、回归科学本质,秉持“慢”的理念。
2007年,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,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、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。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。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,并被觉得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。
记者:在国内的学术圈中,你的论文数目好像并不多?
饶毅: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。论文可以看数目也可以看水平。假如用《让子弹飞》来比喻,你可以算不少次枪声后击中不少目的,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的。中国目前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,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,而极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的到底多要紧。
我一个人的论文数目比较少,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,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。其中,两篇是神经发育:2005年《细胞》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,2007年《发育生物学》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;一篇是行为,2008年《自然神经科学》报道鱆胺参与争斗。
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《自然神经科学》发表过一篇述评,评论同期一篇文章,虽不是大家的研究,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,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一样的讲解。
而2006年、2009年、2010年,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目为零。
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,可供批判。
记者:我发现有个非常矛盾的现象,你常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,仿佛不低调,但对科学却非常有耐心,又非常低调。
饶毅:不矛盾。我写的中文文章,是为了推进改革、为了改变科学文化、为了让年轻人学生少受不好的风气误导,所以数目不可以太少。而科学是我的本行,不需要在公众中谈。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,而且我倡导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,而不只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。
记者:不少人对你个人实验室的状况也非常不错奇?
饶毅:我的实验室,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,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,迄今为止,速度都不算非常快。
在我的实验室,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爱好和自己动力,学生、技术员都有非常大空间,而且他们多半非常有主见。前不久的组会上,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“好”,实验室别的人员惊讶了半天:仿佛是首次听学生说“好”而不是反驳我。
通常来讲,我的实验室不依靠速度的角逐,而是需要多想,多探讨,选择其他人不太做的范围。
在美国时,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,尤其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。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、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-lavigne同时发现的。
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,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,tessier-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由于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。
1999年大家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《细胞》杂志上。
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,分别发表在《自然》和《神经元》,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用途。由于大家已经做了一些工作,才能在该范围做下去。后来,从1999~2009年十年,大家共发表约20篇论文,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,以slit为主,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,所有这类都集中理解一个问题:导向的分子机理。
记者:回国将来呢?
饶毅:我期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。我回国的时候,估计能做到这点。但,从发表的论文看,我在中国的实验室,论文数目特别少。即便这样,我目前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。
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。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探索了不一样的行为范式,最后大家决订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,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渠道,分析动物间相互用途的机理。这种转型,本身需要时间。大家进入新范围,行为范围的人不熟知大家。行为和发育不同,有不少人工察看的部分。我不放心,要紧实验,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,不可以出纰漏,需要严谨。所以,对于自己实验室的“慢”,我感觉至少在现在是必需的。
记者:怎么样解析这种“慢的标本”?
饶毅:科学研究的慢,不是偷懒不做,而是指要紧的结果出现慢,但研究者积极考虑,积极推进研究。
是不是慢与个人风格和特点有关,也和研究的性质和范围有关。大家实验室由于研究性质、转型、风格、时期等多种综合原因,不可能快。大家不是故意追求慢,是速度不可以做大家的目的,水平和高度更受看重。
在科学界,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。可能可以说,这是学术界都爱的“西施”,大家实验室非常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。
但,我自知不是“西施”,而是有不少缺点的研究者,不可能面面俱到,不可能什么都做好,不可能非常快,也就不适合“东施效颦”。
记者:论文发表的杂志仿佛大伙感觉非常重要,你怎么样看?
饶毅:在什么杂志发表,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水平和重要程度的怎么看。但,它并不是所有同行的怎么看,而是几个审稿人的怎么看,有时可以出现偏颇,而且有空闲问题。所以,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量上说明文章的重要程度,但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。
譬如,神经生物学近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创造是光遗传学,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,创造技术的两篇重点论文,值得获诺贝尔奖,但它们在《自然神经科学》和《美国科学院院报》上发表,而不少有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《自然》、《科学》和《细胞》上。
这是由于刚刚出来时,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立刻意识到其重要程度,而后来大伙非常快都意识到重要程度,所将来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。其他范围也出现过如此的现象,所以,必须要看内容、做学术判断,而不可以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字。假如只看杂志名字,那样大家每个单位就不需要科学家,而可以请中学生来评价科学了。
记者:你是不是也感觉到了一些重压?
饶毅:现在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,对我也不例外。
有人讥笑我老得不可以而回国,有人觉得我只能写博客不可以做科研,有人觉得我做不出科研成就才谈政策……不一而足。
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要紧,而且应该又快又多。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忧。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,不会常常催结果,而是有问题就讨论。
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,只能有选择。
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,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《细胞》论文,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,只须我不怕喝倒彩的重压,不脱离我们的特征转而追求急于求成,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重压。
记者: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,你有什么建议?
饶毅: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讲,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,现在比较难,假如做得慢的,在国内重压会比较大。
我目前想出来讲这类不是我一个人需要特别支持。我同意中国年轻人报的采访,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,期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,尤其是一些青年。在当前情况下,选择出色的人、有潜力的人、积极工作的人,即便他们“慢”,也支持他们,是不太容易的事情。支持快的人,支持错了,也没人责怪。而支持慢的人,也会有搞错的时候,作为各级资源学会者、决策者,这好不容易。
但,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大家:以后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,既可能源于快的渠道,也会源于慢的方面。因此,不一样的科学工作者依据各自特征,有所选择,有得有失。